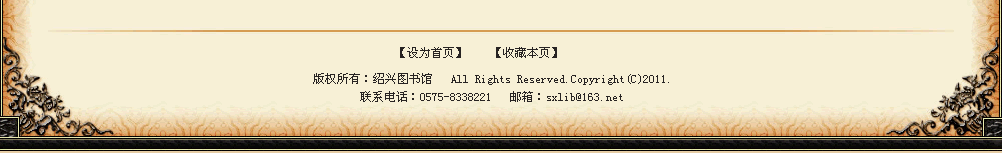绍兴人希望把禹祭和鲁迅、兰亭书法节等传统的文化资源结合起来,做成三位一体的旅游资源。但外地人知道得最多的还是黄酒、水城。即便升为国祭,大禹在4000年后能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仍旧无法预计。
绍兴之小,从公交车站的站牌上就能看出来,十几站就能贯穿全城。出租车最多的地方是在长途客运站,司机们都在这里等待外地游客,如果游客走得远,他们可以赚到40来块钱。本地人是不坐出租车的,只要上公交车,20分钟就能到家。
司机余绍化每天都要在大禹陵附近来往十几次,用他的话说,虽然要经常空车回市区,但因为“绍兴地方不大,拉个游客过来就几十元钱,算起来也不亏”。随着一年一度的禹祭声势越来越浩大,政府耗费了2亿多资金改建的大禹陵也逐渐为外人知晓。
绍兴的焦虑
大禹陵坐落在会稽山上,在到达山脚之前,就能在几公里外看到山顶上耸立的大禹像,古铜色的塑像被阳光烤得发亮。余绍化说,每年4月禹祭的时候,山脚下的公路都要严阵以待,“省上的领导都要来,去年连中央都来人了”。禹祭被列为绍兴市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点项目,它也正在被塑造成一个精神图腾,不仅市民可以进陵观赏,连一些学校也会在教室里放了电视,要求学生集体观摩。大禹陵的所在地会稽山也在这种氛围下成为绍兴继黄酒、水城、鲁迅后的又一个城市标签。
让当地人不满的是,禹祭做出声势后,一间名叫盈放科技的南京公司抢注了会稽山的商标使用权,把它拿来命名了一款会计软件,这款软件在绍兴的电脑城里也能看到,产品说明上很清晰地注解:“4000年前大禹在会稽山召开的诸侯大会,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会计、审计工作大会”。事件爆出来后,绍兴本地媒体组织了一次讨论和调查,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官员的保护意识太薄弱,重演了端午祭被韩国人抢注的事情,只不过这次抢注出现在人民内部,“大家都是江浙人,也不能说拿就拿”。
2004年,禹祭受到了一次刺激。当时,甘肃省天水市的黄帝公祭被认定为“国家级祭祀活动”。随后,国家重点贫困县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耗资1500万元举办了一次女娲公祭大典(当地政府称“只花了740万”)。此后发生的一切,就像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预测的那样:“炎帝、伏羲、女娲、尧、舜、禹等等,还有大批地方神、民族神、行业神”都进入“政府公祭”的行列,公祭对象的争夺战拉开帷幕。
在绍兴市宣传部副部长孙杨看来,外界对禹祭的误解太多,其实绍兴市政府本身的想法很简单:“绍兴在长三角地区,也算富裕的城市,人均生产总值今年应该可以突破5000美元。但这些GDP大多都来自于制造业,因为油价和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制造业的利润很难有大幅的增长,其他产业,绍兴最方便做的就是旅游。但你说,水城、鲁迅什么的,全国人都知道,很难再有兴奋点,大禹文化是最切实可行的项目。”
绍兴第一次大规模地举行禹祭是在1995年,在祭祀的次日,工商局居然接到上百个注册申请,要求注册带有“禹”字的商标,最终通过了其中30个。如果说之前禹祭还只是半民间半政府的祭祀活动,但企业那嗅觉灵敏的投机行为则彻底触动了政府的神经,以更官方形态开展禹祭逐渐成为绍兴的城中大事。也正是从1995年开始,大禹陵的恢复和扩建工程正式上马,直到2006年才告一段落,前期的投入已经无法计算,而从2001年开始,投入的资金超过2亿元。
最早,绍兴市政府只打算恢复在文革期间被损害和因年月久远而遭腐蚀的设施,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禹庙。“禹庙的彩绘大部分是清代绘制的,其他部分是民国年间绘制的,因为部分色彩已经粉化脱油,只能全部重绘。”孙杨介绍说。为了保证效果,彩绘工作的负责办公室特别邀请了全国知名的河北承德市文物局古建队前往绍兴施工,随后,大禹陵又在当年进行了其余的修复工作,共花费3000万元。
所有的成本投入都和这个城市的焦虑息息相关,孙杨自己也能体会这种焦虑背后的诱因:“和周边城市比,绍兴的优势越来越小。杭州、宁波都市圈的‘两极优势’正在得到强化,温州、台州有港口,临港产业发展得很好。嘉兴作为接轨上海的前沿,融入长三角的区位优势也比绍兴强,甚至连金华,因为是浙中城市群的核心区块,在全省的规划上可以占很多便宜。绍兴如果不想单纯依靠制造业,走文化旅游的路是必然的。”这个“必然”带来的是随即轮番而上的大兴土木,会稽山可能是绍兴10年来变化最大的区域之一,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有庞大的扩建项目实施,有时候是多个项目同时进行。最初,绍兴是想力推大禹,但在被甘肃抢先成为国祭之后,市政府希望把禹祭和鲁迅、兰亭书法节等传统的文化资源结合起来,做成三位一体的旅游资源。但孙杨自己也承认目前一切都还在纸面上,外地人知道得最多的还是黄酒、水城,“禹祭还要很长时间的培育期”。
升级禹祭
生于四川汶川的大禹,在全国十多个省都有遗迹,在确定力争把禹祭升为国祭后,绍兴市文旅集团特意派人考寻过在绍兴境内,大禹究竟有多少遗迹。大禹陵景区的负责人王水良也参与其中,最终的结果是,绍兴境内的大禹遗迹共有八处,从萧山县与绍兴接壤处的“夏履桥”到湖塘镇的刑塘,整个遗迹分布在绍兴地图上排成一条对角线。这个结果让市政府尤为兴奋。
在巨额投资扩建大禹陵后,升级禹祭成为势在必行的一步,从2001年起,活动进入白热化阶段,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由于活动上有大量表演,保证禹祭期间全市电力优先供应会稽山已经成为当地政府秘而不宣的指令,每年4月,类似“关心禹祭,确保电力”的报道总会见诸媒体,“每年一小祭、五年一公祭、十年一大祭”也正式成为一个需要执行的文化政策。在王水良的记忆中,2006年到2008年的祭祀活动最为盛大,说起来,其实每年都是大祭:“一般表演人员都有3000人左右,来看的差不多上万人,司机根本不敢走这边拉客,水泄不通。”在王水良看来,2006年,禹祭把规模效应做到了极致,并且得到了省里的重视,他的其中一个理由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特意给绍兴市领导班子写信,希望把禹祭坚持下去,做好。这封信的原文被绍兴电视台在新闻中播出,市政府也得到极大鼓舞,升级禹祭的动作也加快。
王水良介绍,禹祭的仪式十分讲究。祭祀典礼从9点50分开始,意喻大禹为“九五之尊”;随后鸣铳9响,赞美大禹平洪水、定九州的不朽功绩;鼓手擂鼓34响,表达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先贤的缅怀;撞钟13响,传达13亿中华儿女对先祖的绵绵追思。这些程序都被刻在大禹陵各个景区的道具牌上,但一些资料也没有更新,禹祭广场的牌子上还刻着“撞钟12响,传达12亿中华儿女对先祖的绵绵追思”的字样,没能跟上中国人口增长速度。
明年的禹祭目前也已经进入筹划当中,王水良和孙杨都不愿意透露当中的细节。另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是,禹祭13年,究竟给绍兴带来了多大的经济效益?孙杨更愿意把无形资产看作是禹祭带来的良好效应,这当中包括社会影响,也包括很多来大禹陵寻根的海外人士,在他的构想中,这些人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投资者。但禹祭带来的有形变化仍然无法看见,目前,这座城市最高的楼是四大银行和人民医院,因旅游而带动商业还依旧是个愿景。王水良也承认,除去禹祭的时候,大禹陵每天接待的游客人次很难超过两位数,50元的门票,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价格不菲。
大禹后人
关于禹陵村,当地无人不晓。按照公认的说法,这是一个古老的村落,专为守陵而建,里面两年前还生活着15户姒氏人家,他们都是大禹的后代,4000多年来祖祖辈辈一直在为大禹守陵,现在村子里最年长的是大禹的第141代后人。
禹陵村就坐落在禹祭广场外围,但现在已经看不到任何村民,在一次次拆迁和改建中,村民们已经被尽数搬迁。现在的村子已经被改装一新,所有村屋全部被涂成黑砖白墙的徽派建筑,都挂上了朱漆门匾,上面“禹氏茶馆”和“游客服务中心”的字样显示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商业区。所有的商铺都门面紧闭,只有一间茶楼在营业,老板娘许玉怀是最早租下门面的投资者之一,但她也很少回到铺子里,因为“除了禹祭那两天,其他时候基本上看不到人”,为了节约成本,她的茶楼在为数不多的开门时候也不卖茶,只卖各种罐装饮料。
许玉怀是南京人,嫁到绍兴已经17年,顶下这间铺面的时候,夫妻俩都很兴奋,因为去年的禹祭实在太轰动,几乎全城出动观礼,虽然当天挤进广场观礼的只有几千号人,但更多的市民还是在典礼结束之后蜂拥而至。鲁迅故居和蔡元培故居在文化名人效应中已经不复当年之勇,而禹祭作为政府力推的旅游牌,在得到文化部的许可、升级为国祭之后,大禹陵理所当然地会成为绍兴的新名片,前景看好。为了保证投资的正确,夫妻俩还查过禹陵村历年的改建记录,“最早的时候是1995年,当时闹得很大,虽然报纸没说,但大家私底下议论很多,因为拆村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1995年年初,为公祭大禹扩建禹庙广场,50户姒氏旧宅要拆除,年关拆屋在绍兴人看来不吉利,但在政府的要求下,姒氏族人没有太多异议,12天全部拆完;1996年,为建禹陵旅游区,要迁移大禹山上的旧墓,其中不少是姒氏祖坟。迁坟行动终于引起村民的不满,和政府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最后以政府出钱补偿,并指定了一处公墓区,保证今后不再重迁了事;2001年, 禹庙广场绿化,又一部分姒氏旧宅按期拆完。历次拆迁下来,村子已经被建成全新的地产项目。尽管在绍兴市的各种旅游宣传手册上,禹陵村仍旧被作为4000年来中国第一守陵村推介,但其实,姒氏人家已经和村子没有了瓜葛,对于投资者来说,这则是个好消息,政府的投入和决心都意味着改建后的禹陵村会成为一个大型商业园区。但出乎许玉怀预料的是,目前的生意额都要指望禹祭。“等所有店面都开业后会好一点,真正做起来可能还要两年多时间。”
目前禹陵村的原有村民已经被迁到大禹陵景区之外,两地相隔并不遥远,穿过一条马路再步行10来分钟就能到达。姒大牛是去年搬迁出来的村民,尽管住进了楼房,但他对于自己回大禹陵还要买门票耿耿于怀:“在里面住了60多年,现在回家居然也要买50元的门票。”后来有同住一楼的村民告诉他,禹陵村靠马路的村口没人把守,也没有售票点,可以自由进入,但他依然不愿回去。对于大禹陵的现状,姒大牛最愤愤不平的是,如今的大禹陵景区的工作人员已没有一个大禹的后人,而这也和他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
1997年,姒大牛在大禹陵当过一年的副所长,当时归绍兴文物管理处管,后来市政府成立了绍兴文化旅游集团公司,大禹陵也归该公司管理。至于离开大禹陵的原因,姒大牛认为自己的身份遭到妒忌:“当时我是副所长,但是外面来的记者、专家听说我是大禹后人,都来找我,把正所长晾在一边了,他当然不高兴;后来我干脆就离开了。”现在姒大牛是绍兴文化旅游集团营销部的一名普通职员。他曾为这点和单位交涉过,对方答复他,因为他是农民,没有编制,事业单位无法聘用。如今,每当有专家到访,姒大牛还是会被委派作陪,因为大禹后人的身份,在禹祭的时候,他也会被邀请在广场上敲锣,姒大牛对这些事情仿佛已经心生厌倦:“有一种作道具的感觉。”
按照姒大牛的说法,整个耗资两亿的大禹陵扩建工程在某种程度上都在伤害姒氏一族:“整座会稽山都是大禹的陵墓,并不只是那一块墓碑,但有人修了一条山路一直通到山顶,这不是把我们祖先的陵墓剜了一道伤疤?把大禹陵一分为二了?”他自己也知道大禹文化会继续成为绍兴的头号旅游项目,但已经提不起兴趣,年初的时候,当地电视台播出新闻,有公司愿意出钱拍摄电视剧,讲述禹陵村村民守陵的故事,演员圈定为赵薇和邓超,力争进入中央台播放,他侄女向他说起这件事,他淡淡地回答:“这和我们300多人没有关系。” 最近大禹陵景区开始邀请一部分村民回村居住,参与建设民俗生态区,姒大牛也拒绝了,因为他听到了一项规定:“凡回村居住的村民,必须允许游客参观自己的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