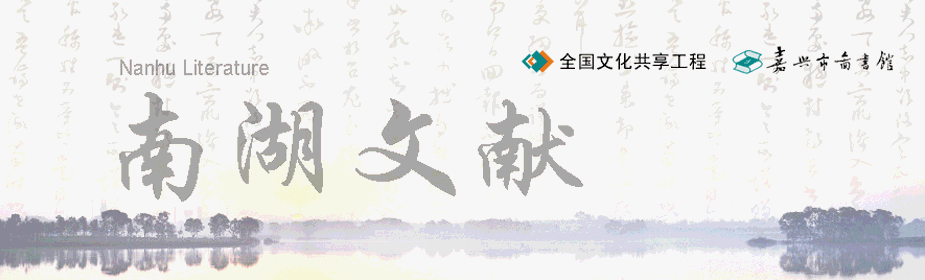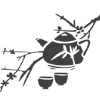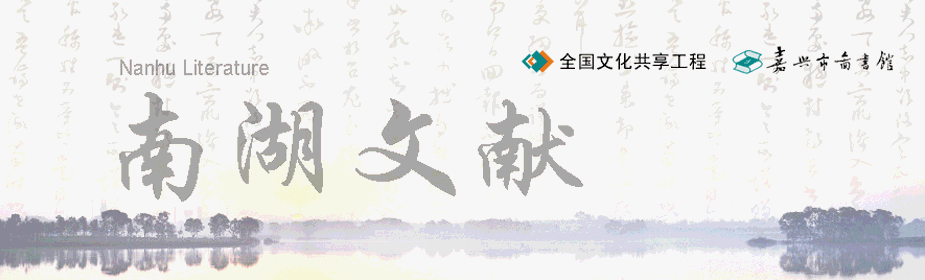明代中期至清前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丝绸贸易的兴盛,嘉兴府城日趋繁荣,商业区与住宅区向城市南部、东南部和东部扩大,城内外有二十四坊三十七巷。明后期嘉兴城内有户口的居民在四万人以上。明万历《嘉兴府志》称嘉兴为“泽国之雄,江东一大都会”(《嘉兴市志》)。在这个背景之下,重建一方名胜烟雨楼自然成为当时的应有之举了。
赵瀛,在嘉兴烟雨楼史上,是一位应该被铭记的功臣。他是陕西三原人,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来嘉兴任知府。当时,市内河道从永乐年间疏浚以后,又有一百多年未曾疏浚了。河道的淤塞影响到百姓的生活。赵瀛主编、赵文华总纂修的嘉靖《嘉兴府图记》说:“嘉靖戊申春,知府赵瀛修浚内隍,令民出土崇其故址。”万历《嘉兴府志》则更为具体地说明了造楼的前因后果:
……市河两岸结屋如鳞次。于是土苴填委,支渠积渐成陆,而巨流亦或淤涩,居人苦之。嘉靖二十六年,郡守赵公瀛创议开浚市河。故渠之湮废者,浚之;民居之侵隘者,卸之;桥堍之垢滞者,辟之。复令里出一舟,运砂土置南湖中,培为楼址。
这项工程的开始时间是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秋(1547)。赵瀛之所以要在滮湖中填岛造楼,是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主要目的还是疏浚市河,大搞水利建设,发展生产,解决城内百姓的生活问题。但是这一着棋下后,却在有意无意间使烟雨楼获得了新生。
赵瀛发动民工乃至里中百姓,用船将河中淤泥运到滮湖之中,填成一个小岛。终于在一年内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接着他又拟在岛上建造楼台,四周种植花木,但是因为“格于人言”而暂时搁议。又过了一年,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赵瀛在“诸僚佐曰可”和“父老曰可”的民意推动下,开始动工兴建楼台。刚开工,赵瀛却升任山西按察副使,一心系在建造楼台上的赵瀛,想到自己走后,工程可能会延滞下来,于是索性横下心,迟留到楼造好五间,才匆匆忙忙赶去赴任,这在当时嘉兴人、进士范言在楼造好后所作的《重建烟雨楼记》中有记载,“于是迟留再,越月克楼五间。”范言还讲了湖心岛的大小,“积五十尺,广袤三百尺”,又记:
郡守山左赵公,重建烟雨楼成。听选官于乔倪锡等,构亭立名,而俾前进士范言记之。范言曰:乃余读宋名人诗,则知滮湖西,故有烟雨楼云。湖受天目紫云诸水,而汇于郡城巽阳,涵青细碧,若朝若拱,形家以为一方之胜也。钱鏐窃据,赵宋偏安,尝筑崇丘而驾重屋,以便游览。
“滮湖西,故有烟雨楼云”,这句非常重要,明确说明了明代人认为宋代前的烟雨楼是在滮湖西畔,也就是鸳鸯湖东畔的。从此处可见,历代嘉兴地方志都是比较严谨的,说到烟雨楼的起源大都说在鸳鸯湖东畔。关于赵瀛填岛筑楼之事及楼成后的烟雨楼风光,除了范言所记,还有同一时间李春芳的记录。李春芳,江苏兴化人。就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赵瀛开始疏浚市河、填岛滮湖湖心那年,李春芳高中状元,授翰林学士,他后来在隆庆年间任内阁首辅(宰相),那自是后话了。赵瀛当时眼光真是准,烟雨楼刚落成,就托李春芳的同年秀水县令方某、李的业师嘉兴县丞丁某致信给他,请李春芳写一篇记。李春芳“遂不能以不文辞是役也”。这位三十六岁的状元公洋洋洒洒地铺叙开去,从建楼的原因讲到为政安民的道理,又提到新建烟雨楼的情况:
嘉禾旧有烟雨楼,岁深圮废。乃其守左山赵君恻焉,是不可以不复也。相城之南马场湖空弃可塞。会浚河积土充市,运而实之,不旬日而洼者已崇,可四五丈许,广可十七八丈。构楼其上凡五楹,缭以垣围,莳以桃李,轩牖洞豁,而一览嘉禾可尽也,仍其名曰“烟雨”。
当时烟雨楼的朝向是坐南朝北,面向嘉兴城的。粉墙黛瓦,曲廊小桥,幽径曲折的湖心岛风貌开始形成,而烟雨楼又可让人登楼远眺,一览胜景,也使滮湖增添了灵魂式的景观。
明代重建烟雨楼距元末楼毁,已有近百年,但此后近五百年一直到现在,这座让嘉兴人自豪的江南名楼虽然屡毁屡建,却受住了历史的
风风雨雨。嘉靖三十三年(1554),在烟雨楼落成五年之后,倭寇侵犯嘉兴,大概是烟雨楼在滮湖湖心吧,楼却没有被破坏。隆庆五年(1571),当时的浙江兵备道沈奎来嘉兴,见烟雨楼已破损不堪,就组织人员重修了一下,还在大楼南面筑了一座石台。
万历十年(1582),烟雨楼又到了“圮不可登”的地步。于是在前一年来到嘉兴担任知府的无锡人龚勉开始进行集资修葺的工作。和赵瀛一样,龚勉在修烟雨楼的同时,也利用开浚城河的淤泥,加高了沈奎所筑的石台,取名为“钓鳌矶”。意思是嘉兴读书人,在科举考试时都能得中功名,独占鳌头。钓鳌矶筑成之后的次年,嘉兴果然中了一名状元朱国祚,这真可谓效果神奇,于是龚勉又在湖心岛上,建造了一些亭台楼阁,取名为“瀛洲胜境”,还在岛上大兴土木,建大士阁,供奉观音大士;又奉梓潼帝君,设文昌祠;设武安祠,奉关帝;又建浮玉、凝碧两亭,在楼后建栖凤轩,还在钓鳌矶旁挖井,龚勉说,“得泉清冽,颇有惠山泉风味,盖井在湖心,自不同耳”。龚勉规划了岛上十二景,赋诗咏之。这是明代自建楼以后湖心岛最大的改观,岛上香火也开始繁盛起来。龚勉这次重修烟雨楼的影响是巨大的。嘉兴名士、大戏曲家汤显祖的好朋友彭辂特地写了一篇《烟雨楼志后序》,对当时纂修《烟雨楼志》的必要进行了说明,可惜《烟雨楼志》没有流传下来。针对当时有人提出“这么一个楼,无非造几间房子而已,何必修志”的问题,彭辂在《烟雨楼志后序》中,用嘉兴是江南名都、人文鼎盛作了回答,又说:
独鸳鸯、马场二湖,枕郭萦带,洋洋泽国。故昔人以烟雨名楼,置之湖心地肺,爰备壮观,谈者谓嘉之有斯楼,是为子都毛嫱润眉发而华衣履,陈帷帐而置琴筑也。奈为前元所毁。至嘉靖已酉,始有访厥遗址,累土成一洲屿,复建楼于上而仍其故名者。
彭辂说赵瀛建楼之前“访厥遗址,累土成一洲屿,复建楼于上而仍其故名者”,换言之,他们是做了一番对宋元之前烟雨楼遗址的调查研究的。如果宋元前的烟雨楼是吴镇画中的滮湖东畔的“高氏圃中烟雨楼”,那么明人一定是清清楚楚的,还用得着调查吗?调查了以后,才决定累土成屿,建楼于上。这和《嘉兴府图记》对建烟雨楼的说法合拍:“令民出土,崇其故址。”“崇其故址”就是“高其故址”,也就是填高原址的意思。这四个字在以后的嘉兴府县志中就很少再出现,大概后来的修志者认为赵瀛填的湖心岛是五代烟雨楼旧址的说法不太靠谱。其实,五代时的烟雨楼如果也在湖中小洲上的话,对原址的要求不像榫头一样严密合拍的话,赵瀛选的位置还是马马虎虎过得去的。范言不就说“尝筑崇丘而驾重屋,以便游览”么。至少明人认为早先的烟雨楼也是填土成洲后造起来的,所以李春芳的记中写赵瀛“相城之南马场湖空弃可塞”倒是透露了玄机,选来选去,赵瀛他们觉得还是就筑楼在原址附近的马场湖(滮湖)吧。
龚勉的这次修缮,产生了良好的游览效果。万历二十六年(1598),濮院董氏醇伯子,来游嘉兴,作《游槜李记》,其中有一段写游烟雨楼的情节:
既而登“烟雨楼”,四顾湖光,一碧干顷,浩浩荡荡,廖廓无涯,濒湖万家,鳞次栉比,诚一方之大观也。凭栏俯视,前有钓鳌矶,令人有鳌头之想。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嘉兴府知府刘应钶又一度修葺烟雨楼,于是烟雨楼越发声名在外,一谈起山水风光,嘉兴人都以之为荣。文人墨客,流连忘返,“夹岸芙蓉飞紫燕,绕堤杨柳弄黄鹂”,明代和徐霞客齐名的地理家王士性在《吴游草·游烟雨楼以四月望日》中写:
环嘉禾郡城皆水也,其高阜面城而起者,拓架其上为烟雨楼。楼之胜,琐窗飞阁,四面临湖水,如坐镜中。春花秋月,无不宜者。若其轻烟拂渚,山雨欲来,夹岸亭台,乍明乍灭。渔舫酒舸,茫茫然遥载白云,第闻橹声,咿轧睐眄而不得其处,则视霁色为尤胜。
这是何等的美景啊。于是,人文的活动也相继在烟雨楼台前展开。人们在楼台前宴游、看戏,招待宾客,或者寻芳问景,好不热闹。万历三十年(1602)重阳,文学家屠隆在烟雨楼创作并排演了传奇《彩毫记》,演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事。一时间,“楼倚重湖酒百巡”,轰动四方。当时嘉兴知府车大任作有观剧诗,有“烧残蜡炬留欢久,水月空明待去舟”之句,可见这次盛大的曲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曲终人散后,尚且余音袅袅。
万历三十三年(1605),大名鼎鼎的董其昌赴湖北督学,路过嘉兴。嘉兴方面在烟雨楼为他设宴接风,游览南湖。董其昌在嘉兴应该住了些日子,他建议把滮湖作为放生湖,而且付诸的行动很有趣:主动大笔一挥,写下“鱼乐国”三字,对知府车大任说,你看怎么办?车大任于是将三字勒石在烟雨楼前,这就是如今尚存的“鱼乐国”石碑了。
在崇祯五年(1632)时,当时的嘉兴知府李化民又组织地方上重新建造了烟雨楼。按常理来说,这次重建烟雨楼来得比较奇怪,因为从万历年间龚勉重修烟雨楼以后,烟雨楼在明代进入全盛时期,上距屠隆排演《彩毫记》也不过三十年光阴,怎么又会突然要彻底重建?时人岳元声的《重建烟雨楼记》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这段时间内,“近既无贤士大夫之培植,而又多游人散客摧残,颓垣败壁,顿忘旧观。”
看来官方的重视,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必要的,我们看,之前的热闹都是因为知府等官员或参与修建或参与游乐,如果后任的官员不喜欢与民同乐,不给钱维修,而来烟雨楼玩的游客又多,时间稍长楼就“生病”了。正好在崇祯五年(1632)左右,烟雨楼失火,这次大火可能很猛,把整个楼烧毁了。记中说:“而适有斯楼之烬,公(指李化民)慨然嘉惠,欲举而更新之。”李化民在烟雨楼遭到一炬大火后,马上就开始重建,显得雷厉风行,所以岳元声在记中大为称赞他。嘉兴人岳元声是岳飞的后裔,写记的时候正官拜南京兵部侍郎,在这篇《重建烟雨楼记》中,他给出了一个烟雨楼史料上从没有过的重要而明确的说法,那就是五代时钱氏烟雨楼的故址,这个说法为一般志书所不载:
嘉禾之有烟雨楼也,亭亭独立,宛在水中央。故老相传以为五代间事,其楼峙郡之东南,岿然为一方屏障。余阅《图志》,知苏子瞻与文长老曾三过其地,汲水煮茶。后人建亭以识其胜,右尚有煮茶亭址。往事灭没,勿复论矣。
岳元声是岳飞的儿子岳珂的后代,岳珂南宋时住在嘉兴城内金陀坊,是南宋有名的藏书家、出版家。记中所提《图志》,是附有地图的方志,如果是指嘉靖《嘉兴府图记》则不可能,因《嘉兴府图记》传之后世,我们能看到它没有这种说法,所以这部《图志》可能是更早而如今已失传的北宋祥符《秀州图经》或者是南宋乾道《秀州图经》,以岳氏簪缨世家、书香门第的条件,岳元声完全有可能读到这些更早的宋版《图志》,因此按其言推测,钱氏烟雨楼的地址就在壕股塔一带。
考方志所载,嘉兴煮茶亭有四个,相传都是苏东坡的遗迹:一是在景德寺(即茶禅寺)之东禅堂;一在本觉寺,是苏东坡三过文长老时留下的;一在真如寺,又名煮雪亭;一在南湖之心,又名三笑亭。如果以“宛在水中央”而论,那就是位于南湖之心的煮茶亭了。光绪《嘉兴府志》记载:“南湖中,苏轼与文长老三过湖上汲水煮茶(《名胜志》);东坡三过嘉禾,每于鸳湖汲水煮茶,后人建亭湖心,遗址尚存(秀水《李志》);一名三笑亭,董少司马有诗(嘉兴《何志》)”,那么,此三笑亭在哪里?只能是位于鸳鸯湖和滮湖交界处的壕股塔附近。光绪《嘉兴府志》记载:
壕股塔,府南澄海门外隍池中有塔七级,屹然独立于烟波之中。其水弯曲如股,塔高十丈,制极工巧。面湖背城,林木蓊翳。昔贤名胜多构于此。苏东坡与文长老曾过此茶话。
从五代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这其中南湖的地貌或因自然或因人为的原因,发生了很大改变。宋代壕股塔立于水中央小洲上是无疑的,可见那时煮茶亭也在小洲之上。岳元声的这段文字进一步明确证明了五代时期的烟雨楼即在壕股塔左近鸳鸯湖和滮湖的交汇处的判断。
明代烟雨楼的声名传播久远,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张岱晚年在回忆年轻时经历的《陶庵梦忆》中,写了精彩的一章《烟雨楼》,为后人传诵至今:
嘉兴人开口烟雨楼,天下笑之。然烟雨楼故自佳……